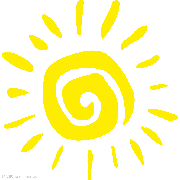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是俄罗斯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著名诗人、散文家、
诗歌理论家。他从很早便显露出
诗歌才华,曾积极参与以诗人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的丈夫)为发起人的“阿克梅”派运动,并成为其重要诗人之一。他早期的作品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后转向新古典主义,并渐渐形成自己
诗歌特有的风格:形式严谨,格律严整,优雅的古典韵味中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文明气息和深刻的道德意识,并具有强烈的悲剧意味。因此,诗评家把他的诗称为“诗中的诗”。诗人一生命运坎坷,长期失业,居无定所,在三十年代创作高峰时,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两次被捕,长年流放,多次自杀未遂,1937年12月27日死于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集中营,并至今不知葬于何处。他的作品曾被长期封杀,直到最近二三十年才重又引起文学界的重视,文集和诗集由多个出版社再版,并译介到国外,渐为世界
诗歌界关注。生前曾出版诗集《石头》、《哀歌》、《诗选》,散文集《埃及邮票》,文论集《词与文化》等。
无题无题岁月难以形容的哀愁沉默敏锐的声音鼓紧了船帆贝壳你的形象飘浮不定燕子我不知道……“林中雪地的寂静中”铁忧伤“尘土的小径通向森林深处”“果实,从树上坠落”“森林中圣诞枞树”“我只阅读儿童的书籍”“如此温柔”“无论什么都不要说”“我拿它怎么办”“当打击和打击相逢”“一种难以表达的悲痛”TRISTIA“微弱的光线以冰冷的旋律”无题“烛光下甜蜜地思索”世纪“不,我从来不是谁的同时代者”“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向着坡堤,伏尔加,汹涌吧”
无题
飘渺的,是你那苦行者的形象,
隔着雾,我无法把你触摸。
"天呐!"一句错话我脱口而说,
只因为我不假思索。
神的名字像一只大鸟,
从我的掌中飞跑。
前方移动的,是浓密的雾,
后面,是空空的鸟笼,无鸟。
1912年
张冰译
无题
面包有毒,空气恶浊:
伤口,很难愈合!
被卖到埃及的约瑟,
谁的乡思能比他更多。
头顶天空的贝都因人,
身在马背闭着眼睛,
编撰着自由的壮士歌
怀想仿佛亲历过的传说。
只是多少有点儿灵感:
有人把箭袋丢在了沙滩,
还有人用什么把马交换,
这一下,事件的迷雾才开始消散。
可如果唱一首真的歌,
鼓足胸口,那么
一切都会消失――剩下的
是旷野、星辰和歌者!
1913年
张冰译
岁月我的岁月,我的野兽,谁能
调查你眼睛的瞳孔
并将两个世纪的椎骨结合在一起
以他们的自己血气?
体内高升的血正喷涌而出
从现世的一切的咽喉;
这个寄生虫仅仅在
新的一天的门槛上颤抖。
这个畜生,只要它还余有足够的命数,
就一定要背着自己的脊梁直到最后;
且有一个波形游走在
一根看不见的脊骨之上。
再一次,生命的顶点
象羔羊一样做了牺牲,
宛如一个孩童的柔弱的软骨--
地球的婴儿时代。
为了从囚禁之中夺回生命
并开创新的天地,
打结的日子的外表
必须由一支笛子的歌连在一起。
是岁月在卷起波浪
用人类的苦难;
是草中的一条蝰蛇在呼吸
岁月的金色的尺度。
而那花蕾还会长大,
琮绿的胚芽也还会萌发。
但我美丽的,可怜的岁月啊,
你的脊骨已被打碎。
当你回首,是那样残忍而脆弱,
带着一个空泛的微笑,
象一只曾经温良的野兽,
在自己留下的蹄印一边。
阿九译
难以形容的哀愁
难以形容的哀愁
睁开一双巨大的眼睛——
花瓶醒了过来,
泼溅自己的晶莹。
整个房间充满倦意——
好一种甜蜜的药品!
这般渺小的王国
吞食了如此之多的睡梦。
份量不多的红酒,
还有少许五月的阳光——
几根纤细白皙的手指
掰开一块薄薄的饼干。
(吴迪译)
沉默
此刻她还没有诞生,
她是词句也是音乐,
她是一个未解的结,
联结着一切生命。
大海的胸膛静静呼吸,
白昼亮得如此疯狂,
盛开着海沫的白丁香
在蓝黑色的玻璃盆里。
但愿我的口学会沉默——
回到沉默的泰初,
宛如水晶的音符,
一诞生就晶莹透澈!
留作海沫吧,阿芙洛狄忒!
让词句还原为乐音,
让心羞于见心,
而与生命的本原融合!
(飞白译)
敏锐的声音鼓紧了船帆
敏锐的声音鼓紧了船帆,
张开的眼里填满了虚空,
深夜鸟雀的无声的合唱
在寂静之中徐徐地浮动。
我像自然一样贫穷,
我像天空一样单纯,
我的自由虚无飘渺,
犹如深夜里鸟的声音。
我看到月亮不再呼吸,
苍穹比裹尸布更没生气;
虚空啊,你的可怕的病态世界:
由我来接待,我来医治!
(吴迪译)
贝壳
或许,并不是你需要我,
一个夜晚,从宇宙的深渊,
一只不带珍珠的贝壳,
我被抛上了你的海岸。
你淡漠地揉取泡沫,用那浪花,
你只顾自己在固执地歌唱,
但是你会爱的,你会评价
这只无用的贝壳对你所说的谎。
你会紧贴着它,仰卧在沙滩,
身上还裹着你原先的衣裙,
你会和它连结在一起,要分也难,
被那水浪奏出的洪亮钟声。
于是,一只外壁松脆的贝壳,
恰似一间空荡的心的小屋,‘
被你充满了,用喃喃的泡珠,
用轻风,用细雨,用海上迷雾……
(智量译)
你的形象飘浮不定
你的形象飘浮不定,令人痛苦,
我透过迷雾,不能把它清晰地触摸
“上帝!”——我不慎脱口而出,
我心里原本并不是想这样说。
上帝的名字,如同一只巨大的鸟
从我口中挣脱,飞出我的前胸。
我面前,是层层的浓雾缭绕,
而我身后,是一只空着的牢笼。
(智量译)
燕子
我似乎忘记了我想说的那个词儿。
一只瞎眼的燕子回到幽灵的皇宫,
以折断了的翅膀,去戏弄晶莹的一群。
在无意识唱着歌儿把夜晚赞颂。
没有鸟鸣。蜡菊不会开花。
夜之马群有着晶莹的鬃毛。
空空的木舟在干涸的河上漂游。
在蚱蜢中间这个词儿把意识失掉。
它慢慢地生长,就僚天幕或庙宇,
一会儿装扮成疯狂的安提戈涅.
一会儿像死去的燕子坠向脚边,
带着冥河的温柔和绿色的树叶。
噢,假若能挽回有视力的手指的羞耻!
挽回相互理解时的凶凸状的快乐!
我如此害怕缪斯九神的号啕,
害怕浓雾、丁当和断折。
凡人具有爱和理解的力量,
对他们说来,声音也从手指间流动,
但我忘了,我想要说些什么,
无形体的思想将回到幽灵的皇宫。
晶莹者说得始终文不对题,
还有安提戈涅、女友和燕子……
但在嘴唇上,就像黑色的冰块,
燃烧着冥河丁当声的回忆。
(吴迪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这支歌儿开始唱起?
窃贼是否在上面沙沙作响,
蚊子大公是否嗡嗡咿咿?
我不想把任何话语
再一次地诉说一番,
也不想喀嚓划着火柴,
用肩膀去推醒夜晚。
真想一垛一垛地摊开
空气的圆顶,让它受难;
真想把装着和兰芹的袋子
一点一点地撕碎、拆散。
以便找到枯草的鸣啼,
透过草房、梦境和世纪,
寻回已被窃走的
与玫瑰血液的联系。
(吴迪译)
“林中雪地的寂静中”
林中雪地的寂静中
回响着你脚步的音乐声。
就象缓缓飘移的幽灵,
你在冬日的严寒中来临,
隆冬象暗夜一样,
将穗状的雪串挂在树上。
栖息在树枝上的渡鸦,
一生见过许多事情。
而那翻卷的浪花
渐渐在梦中成形,
它富有灵感而又忘我,
正要打碎刚刚冻结的薄冰。
在寂静中心灵已经成熟,
这薄冰来自我的心灵。
1908-1909
(刘文飞译)
铁
岁月流逝如铁的队伍,
空气充满铁球。
淬火水中的铁无色,
粉红的梦留给了枕头。
铁的真理――惯于妒忌的
雌蕊是铁,子房是铁。
铁中的
诗歌铁一般地
在分娩的裂口中泪流。
1935年5月22日
(刘文飞译)
忧伤
我学会了离别的学问,
在不戴睡帽的夜的怨诉中。
犍牛在咀嚼,等待在延续,——
城市的警觉之最后一刻钟,
我崇敬那胸鸡之夜的典礼,
当哭泣的眼睛望向远方,
举起道路之忧伤的重负,
女人的哭泣混淆于缪斯的歌唱。
谁能理解“离别”这个字眼,
什么样的分手在把我们等待?
当火光在卫城上燃烧,
胸鸡的惊叹向我们预示怎样的未来?
当犍牛沐浴新生活的霞光,
正在棚里慵懒地咀嚼,
胸鸡,这新生活的代言人,
为何在城墙上拍打翅膀?
我喜欢纺线的平凡,
梭儿往来,纺锤在鸣响。
看,犹如一枝天鹅的羽毛,
赤脚的杰利娅迎面向你飞翔!
哦,我们生活的基础多么贫乏,
生活中欢乐的语言多么苍白无奇!
一切自古就有,一切又将重复,
只有相认的瞬间才让我们感到甜蜜。
但愿如此:一个透明的身影
在纯净的陶盘上卧躺,
像一张摊平的灰鼠皮,
一位姑娘俯身在把蜡烛打量。
不是我们能猜透希腊的混沌,
蜡对于女人,和铜对于男人一样。
命运已把我们投向战斗,
而她们占着卜将目睹死亡。
(刘文飞译)
“尘土的小径通向森林深处”
尘土的小径通向森林深处,
四周寂静而又空旷。
故乡,流淌着丰足的泪水,
她睡着,在梦中,像无力的女奴,
等待着未经体验的痛苦。
看这白桦哭泣着开始发抖
有时还会突然地战栗,
阴影覆盖散乱的道路:
是什么在爬动,行走如雾,
是什么引起这种恐惧……
带着骄傲的风度、殷实的表情……
双脚直插于马蹬。
马蹄踏起灰色的尘埃,
车辙使路面坎坷不平……
大家都在驯服的良马上坐定。
他们没有终点。更尖的长矛
在阳光下闪亮。
空气中弥漫歌声和叫喊,
如同金莲花般粗野疯狂,
黑色的眼睛也在放光……
滚开!不要骚扰虚无的快乐
这是垂死的,奴隶的梦境。
很快那新居,盐和面包,
还有农家特产将会令你兴奋……
快把马蹬用力夹紧!
这伟大的爱情的事业
很快也将和野兽的力量遭遇!
很快坟墓将覆盖原野,
而蓝色长矛和枯草又将拥抱
并且浸染着粘稠的鲜血!
1906年
注:此诗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曼氏最早的诗作之一,当时他年仅15岁,但已显露出夺目的
诗歌天赋。
(晴朗李寒译)
“果实,从树上坠落”
果实,从树上坠落
声音谨慎而又低沉,
在不断的歌声中
传来森林宁静的幽深
1908年
(晴朗李寒译)
“森林中圣诞枞树”
森林中圣诞枞树
包着的金箔在闪烁;
灌木丛中玩具狼们
瞪着可怕的眼睛巡逻。
哦,我预见的痛苦,
哦,我自由的平静,
还有那永远微笑着的
死寂的天空的水晶。
1908年
(晴朗李寒译)
“我只阅读儿童的书籍”
我只阅读儿童的书籍,
我只珍惜儿童的思维。
自深深的痛苦中浮现
一切都向着远方散去。
我为生活疲惫欲死,
从那里我什么也不接受,
但我爱着我贫穷的土地,
因为我没有看见它另外的样子。
我在僻远的花园里
荡着普通的秋千。
那高大黝黑的松树
让我想起浓雾的呓语。
1908年
(晴朗李寒译)
“如此温柔”
如此温柔
你的面庞,
如此白皙
你的臂膀,
你离这个世界
多么遥远,
而你的一切——
都无法避免。
无法避免
你的痛苦,
还有你的手指
不会变凉
还有那永不知愁的
小溪的
静静声响
还有你的黑眼睛
望而却步着的远方。
1909年
(晴朗李寒译)
“无论什么都不要说”
无论什么都不要说,
不管什么都不要学,
像黑色野兽的灵魂:
如此痛苦和美好。
无论什么他都不想学会,
不管什么她都不会说,
就像年轻的海豚,
在世界灰色的大海中游动。
1909年.
(晴朗李寒译)
“我拿它怎么办”
我拿它怎么办——这被赋予的肉体,
它仅属于我且如此惟一?
为了平静的欢乐生活和呼吸
告诉我,我该对谁心存感激?
我是园丁,我又是花朵,
尘世的牢狱中我并不孤独寂寞。
永恒的玻璃上已经拓印
我的呼吸,我的体温。
它的上面还镌刻着花纹,
不久前它还无法辩认。
让瞬间的烟雾流过——
但这可爱的花纹不要涂抹。
1909年.
(晴朗李寒译)
“当打击和打击相逢”
当打击和打击相逢
我不幸的上空,
不知疲倦的摆锤摇动
并想成为我的命运。
纺缍匆忙,粗暴地停止
纺缍脱落
不可能相遇,商量好
不应该逃避。
锋利的花纹纠缠在一起
并且一切都越来越急
在英勇的野人手中
淬过剧毒的长矛高高举起……
之九:
在淡蓝色的珐琅上
仿佛四月里的思绪,
白杨树枝升起
于是不觉间黄昏降临
花纹精致而细密,
精细的网格凝固了
仿佛瓷盘上
刻意描绘的图案
当可爱的画家把它
在玻璃的表面描绘
他的心中记住瞬间的力量
忘却痛苦的死亡。
1909年
(晴朗李寒译)
“一种难以表达的悲痛”
一种难以表达的悲痛
打开两只巨大的眼睛
一只花瓶已经苏醒
泼溅出自己的水晶。
疲惫——这甜蜜的药剂
把整个房间充满!
如此小小的王国
竟大量吞食着睡眠。
来点红色葡萄酒,
来点阳光灿烂的五月——
还有,把一块薄薄的饼干掰开来
是纤细洁白的手指。
1909年.
(晴朗李寒译)
TRISTIA
在光头之夜的抱怨声中
我掌握了离别的学问。
咀嚼的阉牛们,延期地等待——
城市警觉的最后时分。
而我尊崇那雄鸡之夜的庆典,
此时,抬起道路重荷的悲痛,
含泪的眼睛眺望遥远,
女人的哭泣混淆了缪斯的歌声。
谁能理解“离别”一词的含义,
怎样的分手我们将面对,
雄鸡的高唱是何谶语,
当卫城在火光中焚毁,
霞光中是怎样全新的生活,
当阉牛还在畜棚中慵懒地咀嚼,
而为何雄鸡,这新生活的倡导者,
在城墙上拍打着翅膀啼叫?
而我热爱纱线的平凡:
梭子飞速来往,纺缍嗡嗡作响。
仿佛天的羽毛,看啊,迎面
赤足的黛丽娅在向我们飞翔!
哦,我们的生活困乏的基础,
语言的快乐如此平淡无奇!
一切曾是往昔,一切又将重复,
只有相识的瞬间让我们的感到甜蜜。
就这样吧:一个透明的人体
在纯净的陶盘上仰躺,
尤如平摊的灰鼠的毛皮,
烛光下俯身,姑娘仔细地端详。
并非我们能预知希腊的地狱,
尤如蜡对于女人,铜对于男人一样。
命运只是把我们投入巨大的战役,
而他们应该在占卜中死亡。
1918年
注:TRISTIA为拉丁语,系“哀歌”的意思。
(晴朗李寒译)
“微弱的光线以冰冷的旋律”
微弱的光线以冰冷的旋律
将明亮播进潮湿的树林。
如同把一只灰色小鸟
我把忧伤缓缓地揣入内心。
对一只受伤的小鸟我能怎样?
大地已经死亡率沉寂无声
从云雾弥漫的钟楼上
是谁摘下了那口巨钟?
苍穹如此孤苦无依,
喑哑着在高空耸立,
恰似一座空洞的白塔,
那里面只有迷雾和静谧。
清晨充满温柔茫无边际
似梦非梦半睡半醒
而困倦不能够消去
迷蒙的思绪一时齐鸣
1911年
(晴朗李寒译)
无题
失眠。荷马。绷紧的风帆。
我已把船只的名单读到一半:
这长长的一串,这鹤群样的战舰
曾几何时集于埃拉多斯的海边。
如同鹤形楔子钉进异国的边界——
国王们头顶神圣的浪花——
你们驶向何方?阿卡亚的勇士啊,
倘若没有海伦,一个特洛伊又能如何?
哦大海,哦荷马,——一切都有被爱情驱转。
我该倾听何人?荷马都沉默无言,
而黑色的海洋高谈阔论
携沉重的轰鸣走近我的床边。
1915年.
(晴朗李寒译)
“烛光下甜蜜地思索”
烛光下甜蜜地思索
虚幻的自由,
——你首先要和我在一起,——
“忠实”在深夜里哭泣,——
不过我要把自己人的王冠
恭敬地给你戴上
为了你真诚地听命于“自由”
如同对待法律……
——如同法律,我和自由
签订婚约,因此
无论何时我都不会
把这轻盈的王冠摘去
我们是否,被遗弃在空地里,
必遭失败而死去,
我们是否为美妙的毅力
和忠诚惋惜!
1915年.
(晴朗李寒译)
世纪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与你的瞳孔直接面对
用自己的鲜血,谁能
粘接两个百年的脊椎?
从世间万物的喉管
建设者的血液哗然奔流
而在崭新岁月的门槛
只有寄生虫在颤抖
凡是生命充斥之处
都应该耸立起一根脊梁
而这根无形的椎骨
却被汹涌的波涛摆弄
这大地上年轻的世纪——
如同婴儿脆弱的软骨
生命的头颅恰似羔羊
再次成为人们的供物
为了从奴役中拯救出世纪,
为了开始一个崭新的世界。
需要用一根长笛
链接起复杂时光的关节。
这是世纪在掀动
人类忧伤的波浪,
而腹蛇在草丛中
呼吸世纪黄金般的容量。
而茁壮成长的新蕾,
绿色的枝芽突然迸溅怒绽
可你的脊骨已被击碎
我的世纪美好而凄惨!
面带一丝无用的笑容,
你回头张望,虚弱且残忍,
如同野兽,曾经那么机灵,
张望自己趾爪的印痕
从世间万物的喉管
建设者的血液哗然奔流
温暖的软骨把燥热的血
和海洋泼溅到岸口
透过高空捕鸟的罗网
从蔚蓝潮湿的冰岩上
冷漠流淌着,流淌着
流淌成致命的创伤
1922年
(晴朗李寒译)
“不,我从来不是谁的同时代者”
不,我从来不是谁的同时代者,
这样的荣誉我不胜任。
哦,我多么厌恶那一个与我同名的,
那可不是我,那是别人。
世纪的主宰者拥有两颗惺忪的眼球,
和一张粘土样漂亮的嘴巴。
但是,他依靠衰老儿子的麻木的双手
正作着垂死的挣扎
我和世纪抬起病态的眼睑——
两颗硕大而惺忪的眼球。
喧嚣的河流向我诉说
那一系列人类激昂的争斗。
一百年前那一张舒适轻盈的床铺
让一对枕头泛着白光,
世纪的第一次醉酒结束,
一具粘土的躯体可怕的伸长。
在全世界喧哗的争战中——
这张床是多么舒服。
那样也好,如果我们的不能创造新的
就把我们和世纪一起锻铸。
而在闷热的房间中,在马车和帐篷里
世纪正走向死亡,那两颗
惺忪的眼球在角质的封缄里
还闪耀着羽毛状的火光。
1924年.
(晴朗李寒译)
“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
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
十步之内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而在某处还用尽半低的声音,
那里让我们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他肥胖的手指,如同油腻的肉蛆,
他的话,恰似秤砣一样正确无疑,
他蟑螂般的大眼珠含着笑
他的长筒靴总是光芒闪耀。
他的身边围着一群细脖的首领,
他把这些半人半妖的仆人们玩弄。
有的吹口哨,有的学猫叫,有的在哭泣,
只有他一人拍拍打打指天画地。
如同钉马掌,他发出一道道命令——
有的钉屁股,有的钉额头、有的钉眉毛、有的钉眼睛。
至于他的死刑令——更让人愉快
还显出奥塞梯人宽广的胸怀。
1933.11
注:此诗的讽刺矛头直指斯大林,对他的独裁统治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也正由于此类政治诗成了统治者对他治罪、逮捕、流放的根源。
(晴朗李寒译)
“向着坡堤,伏尔加,汹涌吧”
向着坡堤,伏尔加,汹涌吧,伏尔加,汹涌吧。
雷霆呵,请击打这崭新的薄板,
巨大的冰雹请砸向窗玻璃,——
请呐喊和敲击,——
而在莫斯科,黑眉毛的你,
把头颅高高地昂起。
巫师把牛奶和黑色的紫色的玫瑰
偷偷地搅拌在一起。
还用珍珠粉和粉扑
唤出冰冷的狗鱼,
轻声地把钳口唤出。
如何成功地——从印度贵族,是从贵族那
获得了如此寒鸦般美丽
阿列克谢,嗯,米哈雷奇,
请解开,请解开这个谜语——
伏尔加呀,请你弄清并告诉我谜底。
真是罪过,真是罪过,——
不平等的两岸相向而立,
朝着高空,朝着高空飞翔
严重失血的鹰们
飞越山头木屋的尖顶……
啊,我不能看见,不能
看见灰绿色的河岸:
疯狂的割草人,
仿佛走过草丛,走过草丛
暴雨将草场压迫成孤形。
1937.7.4
注:此诗为迄今发现的曼氏最后写的一首诗。
(晴朗李寒译)
 收藏0
收藏0